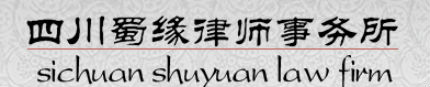“交易习惯”的理解与适用
——陈深红诉劳立宏借贷合同纠纷案(2012)粤高法审监第302号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邓忠开
【案情简介】
2006年6月12日,陈深红向湛江市徐闻县人民法院起诉称,2003年12月3日,我与劳立宏签订一份欠借款对帐表,内容为:2003年10月30日止欠本息323112元,特别约定,劳立宏(债务方)不按月付利息及不按期还本金,其(债权方)可把每月15‰的利息率提高20‰,每月算出的利息后加入本金计复利。2003年12月3日结算后,劳立宏在2004年1月30日还本金300000元,往后我多次催促劳立宏还款无果。计至2006年6月15日止劳立宏尚欠本息65013.08元。为此,请求判令劳立宏偿还借款本金38866.71元及至2006年6月15日止劳立宏尚欠本息26146.37元,若未还清仍按约定利息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劳立宏负担。
劳立宏答辩认为:2002年1月22日,我向陈深红借款40万元,由徐闻县建筑安装集团公司(下称建安公司)提供担保。2003年对帐尚欠陈深红32万元,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和及时履行债务,2004年我与陈深红口头约定以30万元还清32万元的债务,当时有建安公司董事长沈文娱在场。当时我已收回借条,只是忘记收回结算单,我与陈深红不存在借贷关系。至于复利息问题,因不存在债务,所以也不存在利息。此外,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求法院驳回陈深红的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民商事活动中,合同双方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法律,没有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
【裁判理由与结果】
湛江市徐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劳立宏是否还欠陈深红的借款;2、陈深红主张的复利是否合法。根据陈深红提供的证据证明,劳立宏曾经先后两次向陈深红借款共计42万元,劳立宏经陈深宏偿还部分贷款后,双方于2003年12月3日经结算又重新签订了一份欠款对帐表,确认劳立宏仍拖欠陈深红借款本息共计32万多元;该对帐表系双方经结算后自愿签订,双方所设立借贷内容清楚明确,劳立宏并不否认,显然,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劳立宏应给陈深红还清剩余的借款本息。劳立宏辩称已以30万元还清所欠32万多元债务,与陈深红不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劳立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而且陈深红又不予以认可,故劳立宏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得利的,其利率第六条规定的限度的,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双方约定把月利率15‰提高20‰计算复利,即月利率为18‰,此利率并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认定双方对计算复利的约定有效。陈深红请求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5‰提高至20‰,即18%计算复利,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如下:劳立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天内还清陈深红借款本金38866.71元,利息26146.37元(此息已计至2006年6月15日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的利率计付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劳立宏负担。
劳立宏不服一审判决,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
一、其于2002年1月22日向陈深红借款40万元,至2003年12月3日对帐时尚欠陈深红323112元。2004年1月20日经双方协商,同意其一次性以30万元抵销323112元的债务,同时陈深红将借条退还给他,双方借贷的债权债务全部了结。
二、因陈深红担心相关的工程结算期限拖延,多次要求提前还款,后双方和原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沈文娱三方协商一致,由其提前一次性还款30万元了结债务。2004年1月20日其如约履行了还款义务,即双方在对帐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变更,此后,陈深红没有向其和担保人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三、在借贷关系中计算复利以牟取高利是法律禁止的,一审法院认为陈深红计复利并非为牟高利的理由不充分。
四、一审判决认为其还30万元是先还利息后还本金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本案陈深红为提前实现债权,接受其一次性以30万元抵销债务的清偿方式,自愿承担部分利息损失,符合交易习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湛江市中级人同法院二审认为,劳立宏于2002年1月22日向陈深红借款40万并出具了借条,2003年12月3日就偿还借款及利息进行结算签订了一份欠款对帐表,共同确认尚欠本金30万元,利息23112元,并约定徐闻县电信工程结算后还10万元,余下欠款于徐闻县畜牧局综合楼工程结算后付清。劳立宏提出一次性偿还30万元以清偿所欠债务。为此劳立宏于2004年1月20日偿还30万元给陈深红,陈深红收下30万元后将借条退还给劳立宏。但事后陈深红否认当时并没有同意以30万元清结债权债务关系,退还借条是为了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应以对帐表所确认的数额为准,双方债权债务并没有履行完毕就此提起诉讼。综观本案事实,但在还款期限前劳立宏一次性偿还30万元给陈深红,陈深红同时将借条退还给劳立宏,这应视为双方同意全部清结借条所确认的债权债务,而且签订对帐表的同时陈深红并没有将借条退还给劳立宏,以对帐表来确认双方的债务关系,而是在劳立宏提前还款,一次性偿还30万元的时候才将借条退还,从社会交易习惯来看,应视为双方同意以30万元清结借条的全部债权债务。所以陈深红再以对帐表上所确认的欠款余额主张劳立宏承担偿还责任依法无据,不予支持。劳立宏上诉理由充分,二审予以采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判;二、驳回陈深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深红负担。
2012年5月22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在劳立宏提前还款,一次性偿还30万元的时候才将借条退还,从社会的交易习惯来看,应视为双方同意以30万元清结借条的全部债权债务”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劳立宏于2002年2月22日向陈深红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2003年12月3日,陈深红制作了一份(劳立宏)欠借款对帐表,确定至2003年10月30日,劳立宏欠本金30万元,利息23112元。劳立宏确认该对帐表并约定还款期限为:在徐闻县电信工程结算后还10万元,余款在徐闻县畜牧局综合楼工程于2006年3月17日结算,因此,劳立宏于2004年1月20日向陈深红提前一次性偿还30万元,而未按对帐表约定的还款数额、时间和方式清结本案债权债务。因此,二审据此认定劳立宏以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并提前还款的方式结清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并判决驳回陈深红以对帐表确认的欠款余额主张的诉讼请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劳立宏提前还款及陈深红退回原借条,可说明双方重新约定了债权债务,形成新契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维持二审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本案已成铁案。但揣摩、学习此案一审、二审判词,由于当时的法律局限,都有引用“交易习惯”作判,再审虽然刻意回避了“交易习惯”的用词,但不难看出其“维持二审民事判决”,还是依了“交易习惯”。可见“交易习惯”在当时法院审判实践中的作用非同凡响。
《合同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简称规则(一));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简称规则(二))。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1、规则(一)的理解与适用
本条解释规定了两条确定交易习惯的规则:“(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这两条规则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缔约自由”的原则,即当事人只应受其所同意的习惯做法的约束。
a.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规则(一)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的要求有两个:
一个是客观要件,即“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这体现了交易习惯地域性和行业性的特点。
一个是主观要件,即“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交易习惯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交易习惯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某种习惯做法仅仅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被通常采用,则该种习惯做法并不足以被认定是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认定强调该种习惯做法主观上为交易对方(注意用词,非“交易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习惯做法不能约束不知道该做法的对方一当事人。
b.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理解
因为规则(一)所要求的只是“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而没有要求无例外地遵守,所以某种习惯做法只要经常性地被采用,就满足了客观要件。因此,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完全有可能存在几种通常采用的做法,都满足规则(一)的客观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些做法都无法排他地确定,所以当事人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于将某种做法认定为交易习惯就非常重要,是将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习惯认定为交易习惯的基本依据。这种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界定是相当严格的,意味着即使某种习惯做法已经在某地区或某领域、某行业无例外地得到遵守,交易对方仍然只有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才受到这种习惯做法的约束。
c.对“订立合同时”的理解
从交易习惯的时间性特点来看,规则(一)要求交易习惯是“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依据本规则,交易方不得以合同成立后交易对方才得知的交易习惯为依据对其主张附随义务或者对合同条款的某种解释,除非交易对方的“得知”直接体现为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d.对“交易对方”的理解
解释中规定的是认定交易习惯并不要求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时都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某种习惯做法,只不过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一方不得向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交易对方”主张该交易习惯,但这并不妨碍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交易对方”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方主张该交易习惯。
2、规则(二)的理解与适用
在规则(二)中,确定某种做法是交易习惯要求该做法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当事人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直接表明了他们对合同含义的真实理解,所以如果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就可以公平地认为该种习惯做法构成了理解和解释当事人双方表达及行为的共同基础,应当认定为交易习惯。另一方面,交易习惯一经确立,当事人就会出于对该交易习惯的信赖进行承诺,履行附随义务和理解合同内容,而《合同法》则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护这种信赖。
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某种习惯做法可以和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证明交易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来主张该交易习惯;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则只能适用规则(二)来主张该交易习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在当事人先前的交易中出现过一次,一般不宜认定为交易习惯。
3、规则(一)和规则(二)的关系
一方面,规则(一)比规则(二)的适用范围更广,因为规则(一)除了可以适用于多次反复交易外,还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双方的第一次交易。
另一方面,规则(一)和规则(二)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对于交易习惯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规则(一)和规则(二),认定的交易习惯应尽量和规则(一)及规则(二)都能协调一致。如果确实不可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应认为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即认为当事人以意思表示排除了惯常做法的约束力。
4、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
本条解释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的内容应按照本条规定中两个规则的具体要求来确定。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一)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不仅需要证明地方习惯或行业习惯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对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习惯。如果当事人主张依据规则(二)确定的交易习惯,则其应证明在争议案件前双方已经通过经常使用建立了所主张的习惯做法。
另外,因为本条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和第7条的规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严格依照本条分配举证责任。
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此案一审还有一亮点:《合同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
令人羡叹的是一审判决是在此《合同法解释(二)》出台、施行的前两年作出,徐闻县人民法院引用的理由是依交易习惯而推定判决如下:劳立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天内还清陈深红借款本金38866.71元,利息26146.37元(此息已计至2006年6月15日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的利率计付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由此看出,劳立宏于2004年1月20日偿还30万元给陈深红,法院认定的债务清偿顺序是先费用再利息而后本金作出判决。因当时并无《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类似具体明确的法律条文来支撑此判定,故一审被告劳立宏以法院依交易习惯作出判决于法无据,后而具状上诉,也属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