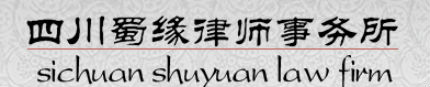[作者] 李春生 ]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正文]
目前,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增加,如何在刑事诉讼体系中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合适成年人”参与刑讯活动这一新机制,能保护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落实我国《宪法》尊重与保护人权的相关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与刑诉法完善等意义重大。
一、我国关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法律规定
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这一规定将1996年刑诉法规定“可以通知”改为“应当通知”,并扩大了到场人范围,进一步完善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此前我国也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条款,例如公安部1998年5月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12条、2002年4月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7条、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4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等文件中,都要求讯问未成年人时,除有碍侦查、调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父母、其他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六部委2010年8月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把律师也列入了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并增加了选任时可以征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意见。
二、我国目前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立法不健全
值得肯定的是,修改后的刑诉法除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之外,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也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这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们也应看到,许多问题还需法律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例如:侦查机关在首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才知晓其为未成年人,遇此情况,是否应立即停止讯问并通知成年人到场?该讯问是否有效?侦查阶段因犯罪嫌疑人不配合,一时不能确定年龄,通过体貌特征也很难确定其是否为未成年人且又联系不到其监护人或其他亲属,此时讯问是否应当推迟或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讯问是否合法以及所取得的口供效力如何认定?讯问人员明知所讯问的为未成年人而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违反此制度的行为应采取何种制裁和补救措施?以上种种情况使得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实践中因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而使效果大打折扣。
(二)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和选任标准不够明确
新刑诉法第270条只规定了“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却没有具体规定居住地基层组织包括哪些,哪些人不能担任合适成年人,如何选择合适成年人,在选择时是否有顺序,是否需要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是否可在中途更换合适成年人,是否对合适成年人的人数有限定等。目前,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标准参差不齐,所选任的合适成年人或素质不高或专业知识不全或主动性不强等,直接影响该制度运作的效果。
(三)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界限模糊
修改后刑诉法仅规定合适成年人发现在讯问、审判中有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但要真正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仅仅提出意见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法律赋予合适成年人更多的权利。合适成年人并不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旁观者”,现在立法的立场是保证一个成年人到场就行,这种立法的思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要明确其有哪些权利义务,同时说明放弃权利和消极履行义务有什么法律后果,让合适成年人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权利,积极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最大化地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深度不够,忽视了制度的保护功能
目前,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重心仍停留在合适成年人一般只参与庭审程序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对审前社会调查、庭审前的教育和宣判后的矫治帮教重视还远远不够。另外,人们往往把合适成年人的功能单一化,即突出强调其教育功能而忽视了同等重要的保护功能。事实上,无论是未成年人在庭审前的恐惧不安,还是在庭审中的紧张害怕,或在被判决有罪后的心理波动,都要求合适成年人充分担当起保护职责。
三、关于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的立法和配套制度
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或者制订配套制度、司法解释等形式,完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细化: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首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才知其为未成年人时,应立即停止讯问并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重新讯问;对于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讯问或者讯问人员明知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而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所取得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一律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立即更换讯问人员,事后对相关违法人员进行处罚,以形成倒逼机制,规范公安或检察机关的取证行为。
(二)从法律层面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建立一支专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
合适成年人的选择,应该从基层组织包括居(村)民委员会、派出所、司法所、共青团、妇联会、关工委等组织和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社工以及各个领域的爱心人士中推选,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选择标准包括品德素质、专业能力、了解未成年人心理、有爱心等方面,司法行政部门定期对合适成年人进行培训,使他们熟悉刑事诉讼程序,正确行使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学会缓解未成年人心理压力,以及懂得相关法律知识。合适成年人队伍还要有具备特殊语言能力、特殊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备特殊案件的需要。另外遇到特殊情况,如需更换合适成年人的,也应当明确规定可以更换。
(三)明确和细化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
对于合适成年人的权利,除了刑诉法中规定可以提意见外,还需赋予其相关的权利。比如,有权向司法机关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有权对相关的公检法人员提出回避;有权审阅讯问笔录,对笔录中记载不正确的地方提出意见;有权对整个讯问、审判过程中侵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提出纠正等。对于合适成年人的义务,除了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理解讯问的方式和程序,向未成年人阐明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协助未成年人与司法工作人员沟通外,还应当按规定的时间到达讯问场所,遵守监管场所的相关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不得非法干扰讯问人员的正常讯问,不得泄露与案件有关的秘密,不得教唆未成年人隐瞒事实等。
(四)实现合适成年人从审前社会调查到判决后矫正的全过程全方位保护
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上,应建立起合适成年人从审前社会调查、庭前讯问、审判再到判决后矫正的全程保护教育机制。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审前社会调查的针对性保护。2、重视庭前讯问的安抚监督,即及时地开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说出案件的实情,同时也要监督讯问人员,防止刑讯逼供。3、审判过程中的感化疏导。4、判决有罪后的矫正方案。另外,要改善制度中保护功能不足的现状,形成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制度机能。
(五)将合适成年人制度纳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体系
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中,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始终是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内容。合适成年人制度在刑讯阶段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体制的探索和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将合适成年人制度纳入法律援助工作的范畴,使之成为一项能够惠及全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