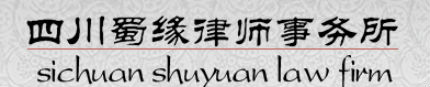【正文】
修改后刑诉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一、对“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认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第139条第1款第1项规定:“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即犯罪嫌疑人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其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以及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犯罪的……”很显然,《规则》明确了认定“可能”的主要依据,即:作案的频率,是否属于惯犯;作案的连续性,行为是否实施终了;作案的方式,是否存在经常变换地点作案;作案意识,主观恶性大,有犯罪的习性,等等。
二、对“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的认定。实践中由于考虑到侦查的效率与秘密性,上述规定很容易被扩大认定。对此德国刑事诉讼法要求,必须是被告的表现已构成毁灭证据等行为的急迫嫌疑,如被告已经采取了相关毁灭、伪造、隐匿证据的预备行为,将以不正当的方法影响共犯、证人或鉴定人,或使他人为此类行为,致使发现案件真相的活动陷入困境。《规则》第139条第1款第3项中规定:“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前或者归案后已经着手实施或者企图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行为的。”该规定实际上从过去(归案前)和未来(归案后)两个方面来考量此种可能性。笔者认为对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性考量,应重点着眼于未来,也即产生现实的对真相调查的阻碍,才具备此一逮捕事由。如果侦查机关已确知证据所在处,通过搜查、扣押等手段即可同样甚至更有效地保全证据时,也就没必要以该事由而逮捕犯罪嫌疑人。
实践中,不能将与证人、共同被告人接触的行为都简单地归为此种情形,犯罪嫌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辩护措施。比如,与证人沟通,使本不欲说出真相的证人说出真相,或询问证人是否还记得事件经过,以寻求有利的辩护方向,等等。这些行为是合法的,不能认定为“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
三、对“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认定。实践中,自杀的可能性判断比较容易认定,“逃跑”的认定要复杂得多,而且,“企图逃跑”历来是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主要事由。国外相关学说与刑事司法实务普遍认为,“可能逃跑”是指被指控人主观上必须认知到自己是在阻碍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并积极追求这一情况发生,才构成“逃亡之虞”.如果被指控人离开住所而没有新的确定住所或者经常更换住所,或者经常外出旅行,但能够随时与之联络上并能随传随到,则不认为是“逃跑”.而如果被指控人使用虚假个人信息或生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或其他足以使追诉机关无法发现其行踪的,自然也是逃跑。认定企图逃跑,必须依照个案的特定状况考量,而不能仅凭判断者的臆测。
【作者简介】
付建恩,单位系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